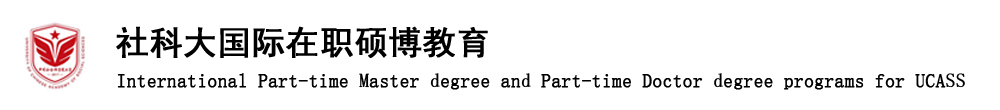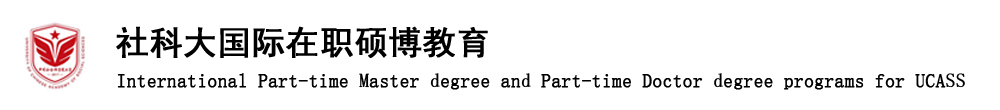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朱彤:能源转型的“小逻辑”与“大逻辑”
2020-11-26 19:09:50 本报记者 宋琪 吴可仲 北京报道
11月23日~27日,由《中国经营报》与中经未来主办的“202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在北京举行。作为年会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1月25日召开的“中经私享会——能源变革闭门沙龙”汇聚了中国能源企业和专家学者智慧,探寻未来中国能源转型与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朱彤在沙龙上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能源转型是从底层逻辑上的转变,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推动能源转型。”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教授朱彤称,能源转型的完整内涵包括“一个目标、三个支柱”。一个目标是指温室气体的减排,我国已经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而三个支柱则分别为: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power to X,即碳中性燃料。
“小逻辑”要服从“大逻辑”
“在进行能源转型相关现实问题分析与政策制定时,不同利益主体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应遵循‘小逻辑’服从‘大逻辑’的原则。”朱彤在发言时表示。
所谓“大逻辑”即为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趋势,以及未来能源系统的基本特征。2020年9月,中央高层公开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朱彤认为,目前,我国能源转型的大方向是低碳和零碳,是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能源系统的转型,特别是电力系统的转型。能源系统的转型意味着我国将从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但这种转变很难通过自然过渡实现,因为这两个系统的技术与经济特征有很大不同。
“可再生能源发电更多是分布式、中小规模、大量的、在用户侧出现的,它的特点是波动性和间歇性,这些都显著区别于传统化石能源,因此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完全不同。目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还比较低,可再生能源还需要依托化石能源系统继续往前走,但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不断提高,传统能源电力系统就需要主动变革以适应。毕竟,在既有的能源系统中,能容纳的可再生能源是有限的。”朱彤表示。
同时,朱彤强调,推动能源转型是实现“碳中和”和经济的低碳转型,构建我国低碳经济竞争优势最重要、最靠谱的路径。也就是说,能源转型背后不仅事关能源系统,还涉及到整个经济的低碳转型,能源转型的成功将为培育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竞争优势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相关方发展的“小逻辑”必须在“大逻辑”的框架下进行。
“小逻辑是不同能源品种地位的变化,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以及以何种技术方案提供能源服务,未来,不同能源品种的发展必须从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角度思考,思考在这样的能源体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朱彤表示。
我国能源转型仍处于初级阶段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教授朱彤还指出,当前需要厘清我国能源转型的发展阶段,这是客观认识能源转型问题、正确应对转型难题的前提。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全球第一,达2.04万亿千瓦时,是美国的2.6倍,同时,我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间接二氧化碳减排16亿吨左右,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也居于领先地位。
“实际上,判断能源转型的阶段应从可再生能源份额看,而不是规模看。能源转型本身是一个国家内部能源品种的替代,发展的量再大,若占的比重很低,也不意味着能源转型进展很快。”朱彤表示。
据了解,2019年,我国风、光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为8.4%,同一时期,美国为9.3%,巴西为9.8%,印度、日本等国家风、光发电占比均不超过10%,欧洲大部分国家则超过15%,德国的风、光发电比例更是突破了28%。此时,若以风、光发电比例10%的分界线划分,我国与美国、巴西、日本、印度等国一样,都处在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在朱彤看来,能源转型处在不同阶段,解决问题的措施重点也不相同。
他指出,根据欧洲的经验,当风、光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不足10%时,电力系统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新增投资就可应对其波动性。例如,可通过优化与周边国家的联络线、提高化石能源发电机组灵活性、增强电力市场灵活度或通过加强需求侧的负荷管理等方式来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这些改善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措施都是属于边际改进,成本很低。
然而,目前,我国在解决可再生能源波动性的问题上存在一定误区,认为储能是解决波动性的最佳路径。
“在我国处在能源转型初级阶段时,眼睛盯在储能上并不合适,它的成本太高,发展储能应该是走上中级阶段之后的事了。”朱彤认为,“虽然解决现实问题时的付出被认为能源转型的必要代价,但这并非现阶段必须要支付的代价,因为有更为经济的解决手段。”
消除转型的政策与体制障碍是“十四五”迫切任务
最后,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教授朱彤指出,目前,成本和技术已经不再是限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我们的问题在于相关政策和体制机制落后于技术可行性,这是“十四五”我国能源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独特的问题:能源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的叠加。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我们的能源行业缺乏市场机制,市场和计划的杂糅带来了不少问题。欧美国家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先于能源转型的,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市场机制也在进行调整,与之相比,我们也需要改变底层运行的模式。
其二是政策,朱彤认为,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重要的不是补贴,而是消除政策障碍,彻底改革旧的体制,将有利于能源转型的新体制构建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是,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的目标不一样的,因此手段也不一样。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而能源转型的目的是去碳。由于碳减排的外部性特征,因此要求政府出手进行一定的干预措施,但是干预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损失效率。
“例如,如果电力市场能实现完全市场化,可再生能源根本不需要小时数的保障,也不用全额消纳。因为电力现货市场的竞价规则是边际成本定价,而风、光发电的边际成本是零,一定是优先上网。因此,加快统一的电力现货市场和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最重要的保障机制。”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教授朱彤解释称。
其三,技术创新的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今天,相比起体制机制,技术其实已经不是问题。而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当新技术出现时,它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不是关键(新技术肯定有弱点),关键是这一技术在未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中是否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未来在能源系统中,并不能简单地只看低碳角度,更要强调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未来,电力系统会被成本很低的风、光发电占据主导,因此电源的灵活性是最稀缺的资源。若一种能源品种同时兼具经济性和灵活性,那么它将是不可替代的。”社科院与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教授朱彤如是表示。
(编辑:吴可仲 校对:彭玉凤)